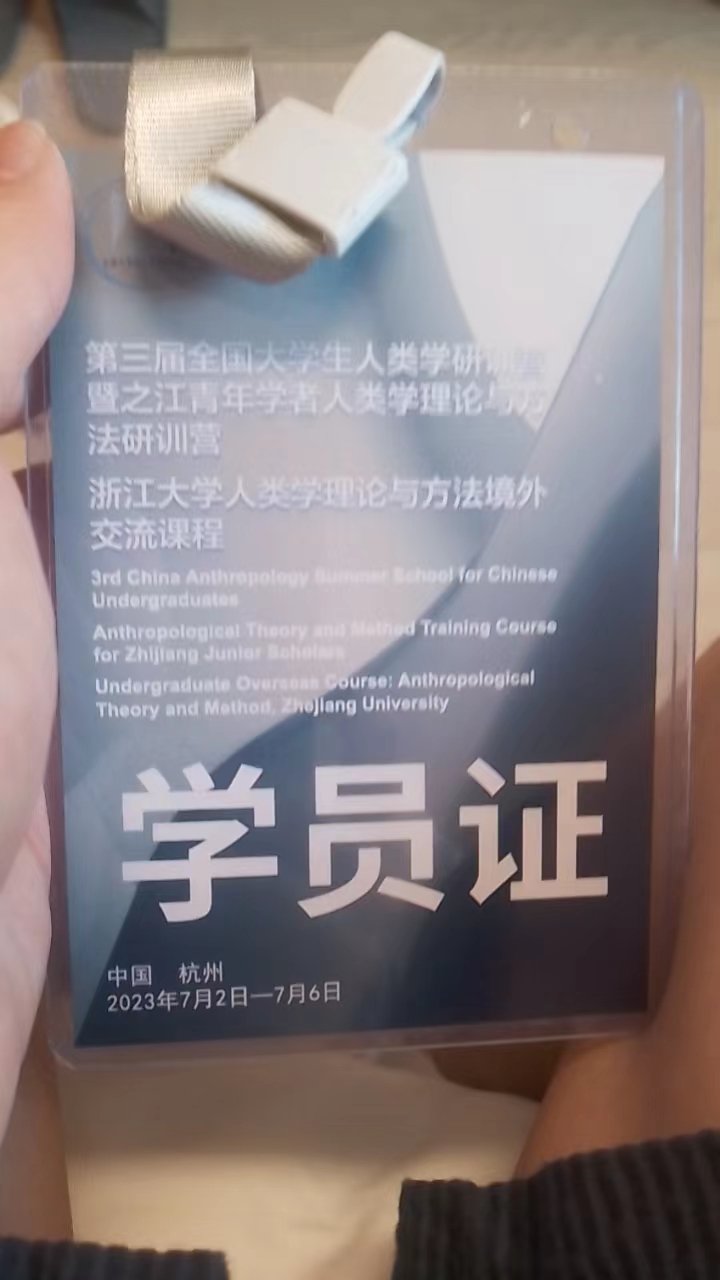
研习和想象中的模样并没有很大差别。
坐在浙大农医馆二楼报告厅,看着演讲台上浙大的校徽,我有点真实但又倏忽间不完全真实的感觉。
今早按照议程走了一遍,先是刘朝晖老师的中文讲座,接着是梁永佳、刘朝晖、阮云星、邱昱、菲利普和徐零零老师与我们的圆桌会议。
遗憾的是我没来得及和老师进行互动就结束了。我不知道自己想问什么,可能因为做的准备实在是不足,我无法对文化遗产的话题进行回应。在梁永佳老师邀请我们选择老师进行「如何成为一名人类学家」这一话题进行提问时,我也没有提问的动力。
直到几位老师大致都讲了自己的遭遇、履历和当下的研究领域后,结合一位同学的疑问,我才稍微在自己的脑子里形成一点散乱的想法。
我想或许可以反对倡导将人类学直言不讳地作为一种宏大的理想,或者说,把自己当作人类学的学生。如何描述呢,应当是……我也不清楚。如果从否定的角度无法阐释清楚,那就从肯定的角度进行解释。
刘老师说自己相对其他「百人计划」引进的老师而言是「土鳖」,本硕博三年都在国内人类学,并且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乡村。他后来提到,学人类学有什么用呢?是啊,学人类学有什么用呢?他不解,为什么当时联合国有一个项目招收的对象必须是人类学专业。
去了以后,他将运河上的人的生活方式、吃喝拉撒呈现了出来。
圆桌会议后,今早的议程也结束了。我离开报告厅,还在琢磨。
我想,人类学或许像「历史尽头灰烬里的余温」,它有关怀,有理想,有某种让人们向往的事物,但它不是在我与他人相互遭遇以及进入田野之前便已存在。
梁永佳老师是有情怀的,他说到自己念本科时想学人类学,但不知道怎么学,幸运的是他的老师会带着他看书。最让我触动的是,梁老师讲到当时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很少见,但他的老师带着他到北京的图书馆借书。不知是什么原因,当时这本书不好借,但他的老师还是想办法带着他去借,并讲了这么一句话:
「如果今天没有读到这本书,或许你就再也不会学人类学了。」
许是因为这样一句话吧,梁老师一直记得,也把这份情怀留在心里,不遗余力地举办了这场第三届全国大学生人类学训练营。起初我还很忧虑,全国只要200人,我何德何能得以入选?入选以后才发现,梁老师似乎并不看重学校出身(训练营的学生院校背景结构很多元),而更在意个人陈述中对人类学、对世界的好奇和热心。为了顺利举办此次训练营,梁老师发动人脉请了牛津大学、伦敦大学、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等等海外知名院校与研究机构的学者(罗兰教授、大卫·帕金教授、范笔德院士和项飙老师等人),给我们送上了这份人类学的盛宴。
我在想,如何成为人类学家,或许是一个理应让人一下子摸不着头脑的问题,就像可爱的菲利普老师一听到这个问题,就摸了摸头,不知如何是好。
我的答案或许就是,我们带着情感来,但不会将它明晃晃地摆在桌上。
幸运,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在这样一个懵懵懂懂的年纪就可以参加各路学者集结的人类学盛宴。
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人类学家,但能接触学习,就已经很好。
我想,我的答案再具体一些,就是切忌高谈人类学的理想,情怀。其实就像邱昱老师说的,在做中非跨国亲密关系的研究时,她的感受是做人类学自己首先是学生,将自己真诚交给别人,在相知相识的过程中相互成全。我结合「不知道人类学有什么用」的刘老师在村庄里完成了三个阶段的论文,想给自己的答案加上一个「不自知的实践」。只管去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才会生成,生长。
写到此次,我想起自己犹为喜欢的《道德的重量》的作者——阿瑟·克莱曼。克莱曼原本念的也只是医学,但却在医学中关注起照护的意义、疾痛的故事,成为了一名医学人类学家。其实很多人类学大家一开始也并非带着一种「傲慢」的态度进入田野,而是首先「赤裸裸」、「纯粹」地进入田野,而后才以独特的叙事方式让外界为他们冠上「人类学」的称号(虽然人类学的出现一开始是为了殖民服务,但后来人类学家反过来为殖民对象奔走)。
人类学的意义不是拔地而起的高楼,而是润物无声之下慢慢生长出来的枝叶。
我再万不可随意将人类学学生这样一个名号挂在嘴上,一方面是自己专业训练与知识远远不足,另一方面我面对田野的态度还没有为实践所生成。在此之前,我相信我只是一个听说过人类学的普通学生,我无法大声宣告它的宗旨,但我能感受到它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