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4年全国大学生人类学研训营回来后,袁老师感觉氛围很棒,便拉了一个和对人类学感兴趣的同学们交流的小群,预计一月一期,开直播和大家聊天。
今晚是第一次直播。虽然这场直播只是与同学们之间的简单闲聊,但我还是想记录一下记忆中的部分话题,并以对我个人而言重要的程度来进行排列。
一、人类学是一种自我教育 #
有人问袁老师,他了解的学习人类学的学生后来都去从事什么行业了?学习人类学让他顿悟了吗?人类学对他来说是一种信仰吗?
袁老师说,坦白讲,至少在中国,学习人类学对求职,或者说对职场的前半期都没有什么作用,他也不认为人类学让他顿悟了,也还谈不上信仰,但人类学对他来说是一种自我教育,人类学具有“扭转”的意识,让原来的看起来是这样的事物不再是这样子。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谈及“过度同情是一种浅显的事物”,以及“同情是一个很简单的情感指向”。对待人与事,我们可能会爱,会恨,会同情等等,但一个人在被爱着的同时,ta也有着可恨之处。
似乎在他看来,好的田野、好的人类学学习需要达到一种对对象和情感更丰富、更有厚度性的认识。
想到自己的时候,我似乎正是“极易同情”的人。当听到袁老师说同情是最简单的情感指向时,我想到的不是对带有这类情感的人贬低,虽然我心中也确实感到遗憾、羞愧。
在我自己原先的理解中,仅仅是带有简单的同情似乎很容易成为袁老师提过的“矫情”,我在此再称之为“滥情”。或许会有点跑题,但还是想说,我一度对部分穿着正式、外表看起来十分精致体面的知识分子有不少刻板印象,其中最显著的是道貌岸然,这或许是因为我将他们与我自己心中建构起来的不体面、受苦受难的普通大众联系起来,同时,我亦认为这些知识分子本该去为这些普通大众发声和服务 [1]
[1] 我又想起前几天在列弛的博客中看的《“为了人民的利益”》,第一次生动地体会到毛泽东的人格魅力,迟一点开一篇新博。
这就是矫情,或者说滥情。我承认,我过去也有过这种举动,这在我两个月前的博文《一步步》中得到了体现。虽然我只是一个无知的学生,而这似乎让我的那些行为看起来更加可笑。即便退一步,不如此斥责自己,我也难以避免地认为这样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意义不大——仅存的意义在于我确实产生了难过的、同情的情绪,我将那一刻的情绪记录了下来,而没有意义的部分则在于,我想到我必然持有通过写作排解这部分情绪,以保有行动上的漠然的意图,以便日后翻看时“抚慰”内心。
但我此刻却觉得不齿。我不过是接受了一点知识教育,便站在一个“高位”去怜悯他者。或许情感本身的存在没有错,但我早先对待它的认识和处理方式,却可能有问题。这已经不只是纯粹的矫情,其实还可能因简单的指向而滑向了虚伪。
这让我想起历史特殊学派文化相对论,这套说辞看起来是如此引人热血沸腾,大义凛然之后,似乎便顺理成章地让人产生同情的情感——一切种族都是平等的,一切的文化都有自身特殊的价值,衡量文化没有统一的价值尺度,应当尊重每一个民族和社会文化。但在现实中,文化相对主义的倡议者们所表现出的矛盾让其本身变成一种赤裸裸的辛辣讽刺,最经典的莫过于亨丽埃塔·施梅勒的命案:
在庭审过程中,如何给凶手量刑成为裁断的焦点,人类学在这个问题上再次表现出符合学科特点的一面。有不少人类学家认为司法部门不应用自己的文化标准去判定印第安人这个被压迫的民族,既然施梅勒与杀人犯共乘一马,那么就应该在印第安文化的脉络下理解这个事实。一些材料声称本尼迪克特告诫联邦探员“不要以美国通行的法律标准和道德标准来评判这件事……施梅勒在接触印第安人的过程中的无意识的行为……很可能引发误会”。在施梅勒外甥的书中,他引用了一封博厄斯写给美国司法部门的信:“我实在忍不住去想是什么样的情况驱使一个有家室、有大好前途的印第安年轻人犯下这样恶劣的谋杀罪?我诚心希望并祈祷他能得到司法上的宽大处理,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要考虑……印第安文化处于被美国文化包裹的弱势境地。”实际上,就连阿帕奇部落的一些上层都觉得人类学过于天真,他们相信施梅勒只是太过相信书本上的内容,无条件地把印第安人看作受压迫的高贵种族,所以当有人提醒她注意安全时,她觉得有必要以信任和良善来纠正官方意识形态对印第安人的污名。人类学或许真的有某种刻板印象,因为相比于相信一个印第安人有可能是罪犯,他们似乎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学生有不为人知的放荡的一面。阿帕奇人指责施梅勒在田野中用富有挑逗性的问题勾引他们的男人,审判长希望本尼迪克特出庭做施梅勒的品德证人,但是被拒绝,因为证明一个白人的品德就是为定罪一个印第安人服务,本尼迪克特担心这会导致印第安部落的仇视,从而让她最重视的印第安研究陷入不确定性。代替她出庭的露丝·安德希尔承认,哥大内部的担心是施梅勒或许真的有不符合伦理的举动。由于哥大方面的沉默,西摩尔一直宣称自己是受到暗示才与施梅勒发生关系,而且受到后者的逼婚和攻击,最终在自卫过程中杀害了她。在逃过绞刑后,西摩尔在一九五七年被保释出狱,但是很快因骚扰一名十岁女童被再次羁押。
—《读书》新刊 | 李晋:将人类学送上审判席的谋杀案
纯粹的概念是“不可靠”的,不可靠的前提往往建立在使用者对它的不加辨别,拿来即用。有时候,我很乐意称部分社会科学学生——同样包括我——为“精神暴发户”。这一概念源于博主心的道理,大致含义是“从别处获取了一些知识,但是超出限度地使用这些知识的人”。我认为,如果只有简单的情感指向,那么很容易为他人所煽动,而对知识只停留在表面的概念,也很容易为其反噬,看似掌握了知识,实则为某些藏在知识背后的意识形态摆弄而不自知,甚至于知识被自身的偏见曲解也不自知。
我早先对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解只有一个面向,只能停留在它自身的内容叙述中。
赫斯科维茨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内容,简单来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内容:
- 所有文化都有独特性和价值,都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并与经济条件相适应,应该用它所属的价值体系来进行评价。
- 某种文化特征在各民族中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本质一致,价值相同,都是为了本群体而服务,例如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和团体起到对内团结本群体,对外表现为一个整体的作用。因此文化谈不上进步或落后,不应该对文化进行“原始的”和“文明的”区别,也不能将“原始的”一词做贬义使用。
- 所有文化都是一个孤立自在的实体,不会重复,不同文化的传统和价值体系无法比较,文化价值没有共同的一般等价物,对不同文化的价值及其产生的文化背景的估价应该是相对的。
且看春花怎么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文化相对论。
人文学科对“文化”概念的使用将富含时间性、权力关系与动态变化的社群表征与实践行为作为亘古不变的本质特征,由此文化从一种活跃着的生命特征转化成了一种固化且无时间的情色玩物。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文化相对主义成为了一种虚伪的政治工具:我们善于用文化来表达明面上的尊重,以此来掩盖内心的冷漠。 ……
……如果说相对主义背后涉及到了自我与他者的交汇,那么在如今许多对相对主义的谈论中,其所采取的是隔阂与分离。一些人口中的文化相对主义将自我和他者拉开,以此在两者间塑造绝对的差异。这种隔离与一种道德虚伪联系在了一起。借用相对主义,它一方面可以对一些不同的群体表现出体恤,或者是更低层次的理解,比如了解有关该群体的知识。另一方面,它为行为主体自身的冷漠免责:他人的文化、观念,恰恰是因为是他人的,所以与我无关,我也不需要了解。
这种自我和他者的分离为“拯救者”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它们在不必要的时候以相对主义体恤他人,然而在涉及到自身时却不予以对方尊重,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站在道德高地的游戏也成了人类学在现代世界骗人的把戏:我们懂得文化,我们尊重他者……所谓的懂得文化在很多情况下是将文化作为习俗、传统、神话、礼仪,让它变成可以收录到博物馆的事项,所谓的尊重他者就是进村搜刮信息,将地方文化视为原生的东西,然后各种历史力量之间的纠结缠绕被忽略。从高明的学者们到学术炼金术的小妖,都多少学会了这样一件事情:“文化相对论既能够假冒谦卑,也可以将知识上的懒惰推卸给相对主义及价值中立,从而保全自己的清白。”
—言之无物 | 虔敬的激情:时隔一年后对Abu-Lughod的阅读
我无法言之凿凿地说明春花便是对的,事实上,我也不应当这么做,只是在他的叙述中,我读到——毋宁说我感受到心中曾经一闪而过的阴霾,那是一种冠冕堂皇,一种不真诚,一种不诚恳,但是人性却很莫名——人不是君子的时候,却仍然希求在他人眼中作为君子的身份而存在。
如果说人类学是一种自我教育,那么于我而言,一部分可能需要表现为一再审视自我对待知识和情感的处理方式。知识是中性物,既可以让人深邃,但也可以反噬,我认为在互联网有许多人带着不完整的知识,给自己刻上了新的偏见,实则沦为他人意志的驱使,而我口中和笔下所宣称和呈现的某种尊重也好、努力也好、同情也好,都可能只是局部的知识和信息驾驭了我之后的结果,那些看似“似乎就是如此”的东西,不仅发生在我们看到的他者身上,同时也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在点评和批判别人的时候,也需要警惕自身。
就此而言,这就是我对“同情是一种简单的情感指向”在意的原因。我想我正在学习的过程中,唯一或许值得宽慰的是在不断想起自己过往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的同时意识到自己的幼稚、鲁莽、甚至是虚伪,我还为此羞愧,并期许着能找到方式不断改进。
二、田野中的痛感 #
袁老师,想问问您如何理解田野中的痛感。可能初入田野的时候很有痛感,但随着田野时长的增加和情感工作,痛感可能有减轻或消散倾向的情况,有时或是感觉承受不了这么多的痛苦。应该怎样处理自己的痛苦与田野深度的平衡?
袁老师大概是说,有“痛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需要将痛感转化为具有生产性的事物。面对痛感,不要过于抗拒,而是接纳。很多时候,一项好的研究,往往正是源于扎入痛感。我记得袁老师还以作为女性的身份为例子,但记不清具体如何展开。
在这部分,我只隐隐约约觉得认同袁老师,但无法用自己的话语表述出来,也不知道以上这简短的记录部分会不会曲解他的意思,期待他下一次直播的分享吧!
不过,谈及所谓的田野痛感,我这时候又想起了春花对自己田野过程感受的记录:
……因此人类学学者,或者说人文社科学者有着一个很强的特质,这个特质在科学的生产主义中很少被提及:人类学学者本身是一种调查工具,它不是量表、不是问卷,而是一个具有自我感觉、自我认识的存在,它会痛苦、会悲伤、会欢乐、会烦闷……人类学调查进行的前提是研究者以自身的人性而成为一种调查工具,而不是因为自己恰巧是一个人,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所以才成为调查工具。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行动者化身为了一种动情的主体,她/他时刻被脆弱性所包围。故而,在调查中,研究者作为人的因素则会影响自身与他者之间的距离:或许是敞开心扉,或许是互相厌烦。这种对距离的洞察与了解,实际上构成了人类学研究的核心。
—散记 | 作为理论的田野调查
我着实觉得这部分讲得真好。
后面提到了田野中的“倦怠感”。袁老师讲出了我曾经有过的感受:初入田野的学生,会觉得田野是神圣的,害怕做不好、辜负,担心无法真正进入田野,无法得到需要的资料,最后成功做出结果。但问题的关键也正是在于,不要太急躁,“进入”田野的前提就是“融入”田野,泡进去,因为在田野中,作为调查者的个体自身也在不断发生改变,应当让自己成为田野这一片经验世界的一部分。
不要一进入田野便认为自己是调查者,马上扑进各式材料,更不要寄希望于一次的访谈、研究方法。允许自己慢慢沉浸进去。
他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调查者和田野对象之间熟悉起来的关系,也如同一位想亲近学生的老师——第一次认识学生的老师便与学生直言相互之间要成为好朋友,相互敞开心扉,这显然不切实际,而更实在的表现则是一起读过书、吃过饭、甚至看过演唱会,如此才可能彼此真正熟悉起来。调查者与田野对象之间也是这样,调查者在还没熟悉、参与和融入田野对象的生活的情况下,如何奢求能接近认识田野对象呢?
虽然我的田野做得比较糟糕,但在三个多月里,我确实感受到后期的状态要比前期更好。
三、知识生产与翻译、出版 #
一位同学给袁老师写了一封邮件,问起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要如何看待知识生产。
袁老师认为,学院的作用在今天已经十分有限,甚至于在对人类学的学习,某些公众号的翻译稿子和文章都要比部分老师接触到的内容更加广泛和前沿。除开学位的文凭价值,硕士唯一的价值可能就在于让人知晓某个学科知识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我认同袁老师的看法,即便我也一直认为这很可能只是我学识短浅,以及身上刻板印象的影响:我国高校内社科的培养体制似乎都很“迂腐”,许多老师或是疲于奔命于发表指标,或是安心待在统一话语的指挥棒下,离学术的前沿已有了许多距离,自身的学术热情、活力也消磨了不少,师生之间没有压榨等不良关系似乎已经很好,难以指望能有多好的引领。而且,人类学也一直在国内出于尴尬的地位,北方已大多数转化为民族研究,或许也只有清华、上海等少数高校和地区还较为跟进前沿。
但,这也只是我的一面之词。所幸在互联网的今天,民间的知识具有充分的可得性。许多不知名的学人会将国外的稿子翻译发到网上,虽然他们或许不具备学院权威认证,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就是民科。按照袁老师的看法,是有效益的知识还是自说自话的民科,一个关键的前提是处理的资料是否正式,民科往往不会处理此类资料。
以我接触到的对象而言,例如公众号“进击的世间师”、“脂肪苦難”(春花)和“陈荣钢”,前两者主要翻译国际的STS和人类学的文章,最后一位翻译各式社科文章,连袁老师也不得不说,在春花那儿看到的许多内容自己都要去补补课,例如像Marilyn Strathern(玛丽莲·斯特拉森)这样重要的人类学家,国内知道的人却不是很多。我关注了春花的公众号以后,也看到许多许多完全陌生,而在国内很少见到提及的名字,例如Lila Abu-Lughod(阿布-卢赫德)、Teresa Kuan(关宜馨)和Saba Mahmood(萨巴·马哈茂德)等等(春花似乎比较关注女性学者)。”进击的世间师“则是翻译日本学者多一些。

不过后来我得知,进击师似乎是读了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两个硕士,春花硕士则毕业于华东师范,陈荣钢则是政治传播学博士。某种意义上,在我眼里,他们的译稿,以及在公众号上发布相关非译稿写作都让我感到很敬佩,甚至要比国内部分老一辈写的论文更有启发性,自觉或许那才是较有水平的人类学学习,我还着实差了太远太远,完整读过的民族志不超双手之数,还有许多没有看懂,遑论英文阅读能力尚且处于起步阶段,来来回回认识的学者也不过马林诺夫斯基、利奇等老一辈——这是基础,但很显然,如果我要继续学习下去,前面的道路还有很长很长,道阻且长。
回到翻译与出版,据说袁老师翻译了四本书,但由于某些原因(例如题材),在国内只能出版一本。不过他认为,现在不少人都自行翻译,而已以各种形式在网上发布,这也不失为一种可行之举。另外,似乎有人提到“薄荷实验”系列的书丛翻译概念看起来有些奇怪,袁老师说到书籍的译者多是非人类学背景出身,或许这是一个原因。
四、公共人类学 #
袁老师认为自己算不上公共人类学,因为他“没有离开自己的行动框架”。按照他的理解,他只是刚好在互联网语境中的人类学方向小有名气的“小网红”,有人愿意请他做分享、参加活动(例如录制播客、线下对谈、分享会等等),仅此而已。但是他并不认同部分同行将在大学讲授的内容——或者是“那一套话语”——拿到公众面前再讲一遍,他认为这样是丢人的,面对公众,就应当使用公众的话语。
我对公共人类学没有概念,按照袁老师的看法,似乎是指以人类学这门学科影响公共领域?袁老师认为,至少在中国,一方面,人类学作为式微的学科,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容易起到影响公众的作用;其次,人类学与其他社科、文科专业一般,在国内的学院体制中资金来源基本都是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教师们往往都是依靠这部分来源运作学科,对公共领域的参与很少。
说起来,所谓公共人类学似乎与应用人类学颇为相似。我能想到的是上海有一家睿丛公司,自称商业人类学,要将人类学用于商业领域中,与复旦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但不清楚他们具体如何进行操作。此外,就是部分NGO、环境保护和社区保护等等。兵哥就没有完全固守在学院体制内,常常是在各个海岛之间走动,与“智渔”有着联系,也作为质兰基金会的顾问,还被邀请上“一席”进行分享。正是因为他与外界的链接,我才有机会与黑石屿结识,后来到西埠村生活了四个多月,从而展开了对于我自己而言的田野调查。
学院与公共之间的分野还是挺大的,至少论文话语就与公众距离很远很远。袁老师虽然自认不属于公共人类学的领域,但是他认为要让知识成为公共的事物,将它传递给大众,我认为至少这也是对公众有益的,相信他的许多分享对听众而言都有所收获。
五、备考中的阅读 #
直播开始不久,便有同学说到在备考人类学研究生,提及在阅读《反景入深林》,觉得是一本很好的书籍,但是不知道怎么结合应试,学习考试技巧。袁老师认为,《反景入深林》是一本人类学意识启蒙的书籍,但如果需要应付实际的考试,还需要针对性更强的教材,例如云大就要求哈维兰的教材。
《反景入深林》让我想起关注的一位公众号的博主,他似乎犹为喜欢这本书,备考硕士期间反反复复阅读,最后考去了中南民大,现在已经读到了博士。他在公众号写的每一篇文章都让我感到对人类学有一股纯粹、干净的情感,似乎和黄应贵先生在书中表现出的情感也有几分相似阿。
春花也对《返景入深林》有着很高评价,但他看不惯部分备考的考生借着这本书“装X”,书籍没有认真读,就把书捧成备考界“网红”。
之后就有人说起备考期间觉得很疲惫,状态不佳,袁老师建议认真阅读大约五本民族志作为调剂。虽然大多数人会觉得备考期间没有充足的时间去阅读,因为有太多的应试内容要背诵记忆,于是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里头。但袁老师认为,不要认为这是无用的,恰恰相反,许多目前看似无用的事情往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他以云大的硕士招生为例,认为国内研究生招生体制矛盾,许多学生虽然考上来,却实实在在地连几本民族志都没有读过。哪怕是备考期间,挑些时间认真从米德那一时期的作品读到最近的《末日松茸》,3~5本书,得到的收获一定远超想象,不管对初试而言,还是对复试而言。
六、本体论转向 #
我一直不懂何为“本体论转向”,对这一概念的接触,似乎还是源于世间师的公众号文章。
由于实在不懂这部分内容,只能贴上袁老师和进击师认为的目前本体论转向综述做得最好的著作,其余讨论已然不记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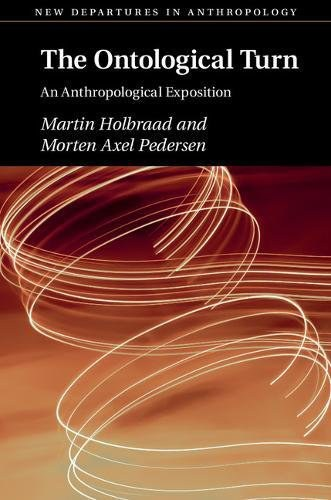
我会有机会、有时间、有能力读上吗?或许不会吧,也或许会。
七、埋下两个坑 #
袁老师为下一次直播埋下了两个坑。
1、分享读书笔记方法
2、细谈“田野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