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以范式和流派的角度来梳理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如同谈及结构主义人类学会想起 Claude Lévi-Strauss(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谈及阐释人类学则必然无法回避 Cifford Geertz (克利福德·格尔茨)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Lévi-Strauss 和 Geertz 似乎可以分别代表整一个结构主义人类学和阐释人类学,同时,他们也各自以杰出的论著和深刻的洞见,对整个人类学学科,乃至人类学以外的诸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期梳理我在阅读中对 Greetz 的认识,以串联过去散乱的知识点。
应当从何说起?我想,已经有太多太多关于 Geertz 的介绍,不妨在此留下我对他印象深刻的地方,结合 Geertz 提出的概念和思想,从我自身出发,而非是对任何教材的复述。
不过,坦诚来说,我最终一定还是无法摆脱对各类知识的抄写、改写和拼接。不过,学习的过程或许也正是在一次次的模仿、思考、修改、再思考的过程中成长——少废话了,写吧。
Greetz 掠影 #
如前所述, Greetz 的影响是跨学科的,他在阐释人类学中做出的努力可被认为是「对话」式的,超越了学术界,扩展到了受过教育的广大读者群体。
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几年后,Greetz 便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为数不多的终身教授,并得到人文学科领域许多学者的认可,例如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欧洲文化史专家 Robert Darnton,当代西方学术界新历史主义批评流派泰斗的 Stephen Greenblatt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与历史学杰出贡献教授 William H. Sewell Jr. ,以及美国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 Natalie Zemon Davis 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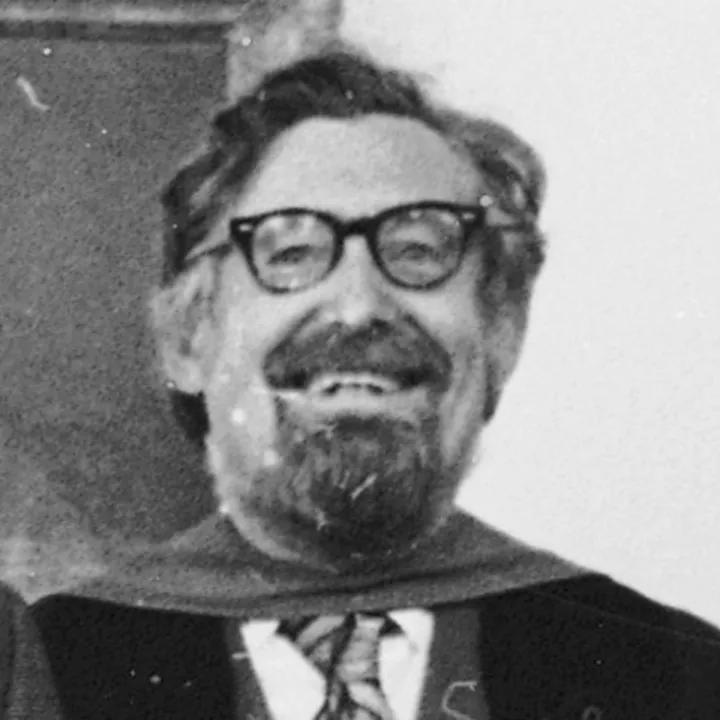
当然,Greetz 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美国人文领域,即便是和美国人类学取向不同的英国人类学界,也充分肯定了他的贡献,为其颁发英国人类学会赫胥黎奖。此外,Greetz 也是当时唯一一位在亚洲获奖的西方文化人类学家——荣获日本「亚洲奖大奖」
这些荣誉集于一位人文学者并不多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好奇 Greetz 都提出了什么洞见。
文化 #
Greetz 认为,文化是当地人背后由人类学家阅读的文本,是一种象征体系。基于文化是文本,人类学研究即文本阐释,通过它,我们可以揭示文化诸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
我所采纳的文化概念本质上属于符号学 [1]
的文化概念,书中后面的各篇论文试图阐明这个概念的功效。我与马克斯·韦伯一样,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这些网,因而认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1] 符号学是对符号与象征的分析。
在这里,因为「文化形态的明确化」是通过社会性行为得以实现的,所以对文化的理解不是凭空的,而要从理解人的行为出发——如同 Weber 强调社会学研究是阐释人的行动一般。
具体来说,由于人的本质是象征性动物,通过象征符号积累经验、进行沟通并代代相传,因而人的行为——文本的符号——也是象征行为。人类学家要做的,就是寻求象征行为背后的意义,了解它是「嘲笑、挑战、讽刺、愤怒或者是献媚」——由象征行为传递的意义进而有机形成的体系就是文化。
由于文化系统的意义由人与人互动的过程建构起来,行动与行动之间的接合、交流、互动形成了一段段对话,因此对某一个行动或文化现象的理解要置于原来的脉络之中。而且,这种理解要致力于追随当地人的行为,从研究者到当地人,然后从当地人再到研究者,反反复复,「进行二次方、三次方的解释」,进而使得当地人的行为成为可阅读的文本。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 Greetz 的文化是被阐释的对象,这其实暗含着与 Franz Baos 文化人类学研究传统的亲近,同时有别于 Tylor、 Lévi-Strauss 或认知主义 [2]
[2] 认知主义或认知人类学强调文化意义是隐私的,在个体认知之中。 Greetz 对此采取的相反路径显然影响着他关于「经验」与「距离」的看法,人类学家「不必成为心灵感应者、精神病医生或间谍」,不必变成当事人。详见后文关于 Greetz 对距离的认识。
这里的文化和 Baos 影响的文化与人格学派关注的不同地方则在于, Greetz 关注的文化是 Wittgenstein 关于符号意义的观点,这意味着关注的并非心理上的表征,而是社会实践的运用——文化存在于公共领域的行为与实践中,人类学家可以观察到这些行为和实践。
厚描/深描 #
厚描/深描(thick description)是 Geertz 在文化人类学中引入的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一个概念——之所以说引入,是因为该概念最早由牛津大学的哲学家 Gilbert Ryle 提出:
对任何特定的(譬如,最初令人感到困惑的或者从表面上看起来是毫无意义的)行为或实践进行全方位的描述,同时提供充足的背景信息,包括地方性的信仰、习俗、价值观以及相关实践,以便读者能够理解这些实践——作为它们所属的生活形式或“文化”的一部分——具有的意义。
Ryle 以「眨眼」这样一个动作作为说明——同样是眨眼,它可能是一次无意识的神经抽搐,也可能是一种暗示。此间不同的是「眨眼」背后的行为意义,「它涉及到情绪、动机、秩序观念以及独特的实在外衣,这些让一个行为具有了独特的真实性」。
而 Greetz 所讲述的民族志的「厚描/深描」,追寻的正是行为背后独特的意义如何发生,而非仅仅停留在对行为的描述上,以及单纯迷恋于一系列的操作过程和技术——建立关系、选择报道人、制作笔录和谱系、绘制地图等等。回到「眨眼」的例子,可以认为,「厚描/深描」要做的,正是以「眨眼」的行为作为起点出发,建构知觉、解释无意识的眨眼和有意识的传递眼色的文化层次。
在这里,民族志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单纯的人类学方法或技术,它实际上还是一种理论,一种与人类学知识生产密不可分的理论,如春花所言——他关于「厚描/深描」的比喻在我看来十分生动形象:
正如 George Stoking 的观点,田野调查早已经超越了一种方法,它早已是“人类学家和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这里的关键是一种知识性努力,通过这种努力,厚描,如同蜡笔一样,一层一层地在民族志的蓝本上涂抹,将研究对象搭建起来。它的每一个图层都承载着人们的观念与行动的依据,在一层一层的叠加中,被研究群体的世界被体系化地呈现出来。
距离:亦远,亦近 #
其实,在「厚描/深描」的基础上,或许可以延伸到一个关于「距离」的问题。
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filedwork),在此基础上完成民族志 (ethnography) [3]
[3] 根据库珀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民族志被认为是一种对当地文化的事件和习俗的内部描写。
[4] 实际上,我认为自己在西埠村做的田野积累下来的所谓「田野随笔」正给了我这样的感觉。
[5] 关于这部分内容,近来易小荷那被认为不负责的写作作品——《惹作》——成为话题焦点,详见公众号「结绳志」文章《反对不负责任的写作——《惹作》在凉山内外的回声》。我也想从此入手,谈及另外一个话题:无用的文科在什么时候有用?
[6] 关于民族志中「距离」的思考,春花的写作给我的感受十分清晰,此处思考和记录,或许是对他思考的模仿——虽然这样的做法很有拾人牙慧之嫌,但我希望能在这个过程中唤起我过去的田野经历记忆,唤起来自我自身的思考,将对他人的模仿转换成「站在他人的肩膀上看世界」。
Malinowski 认为要理解「土著的观点」,即通过所谓「移情」达到从当事人观点看当地文化的境界——这被视为田野工作的最高指导原则。但 Greetz 则认为,「移情」并非要求人类学家变成当地人——事实上,人类学家也不可能变成当地人。
我们在衡量自己解释的说服力时所必须依据的,不是大量未经阐释的原始材料,不是极其浅薄的描述,而是把我们带去接触陌生人生活的科学想象力。
这种所谓的「科学想象力」是一种怎样的表现?
它是带着接触陌生人生活的想象所进行的工作,而为了把握住这当中的标杆,把文化去视为符号系统是一种难免的手段,通过将文化当中的各种因素分离,说明它们的内部关系,并叙述其特点,组织核心符号以及作为外部表达的基础结构,据此理解对方的意识形态,从而完成阐释的工作。
这样的回答看起来仍然是抽象的。在这里,我认为一个吸引人的答案并非是对于「科学想象力」的事实性回答,而是关于田野中对距离的价值性认识——我必须承认,我无法理解和准确回答「科学想象力」,但就此,我认为如何看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更加重要,更值得我们去思索:
人类学学者本身就是一种调查工具,它不是量表,也不是问卷,而是一个具有自我感觉、自我认识的存在,它会痛苦、会悲伤、会欢乐、会烦闷……人类学调查进行的前提是研究者以其自身的人性而成为一种调查工具,而不是因为自己恰巧是一个人,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所以才成为调查工具。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行动者化身为了一种动情的主体,它时刻被脆弱性所包围,因而,在调查中,研究者作为人的因素会深刻影响自身和他者之间的距离:或许是敞开心扉,或许是相互厌烦。这种对距离的洞察和了解,实际构成了人类学研究的核心。
Marjorie Shostak 在《妮萨:一名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中似乎为我们展示了在这一方面中的努力。和 Paul Robinow 一般,Shostak 毫不避讳地在书写中呈现研究对象和自我的声音,被研究者不再是一个被动等待速写的素描画,而是一个带着理性和情感面对着人类学家的人,同时,研究者亦因此而产生诸种情绪。
她的声音很大很尖,有点狂暴,老想引人注意,没个消停。每次,只要引起我的注意(甚至经常在我不注意她时也如此),她就要谈南希和理查德。我的害怕很快变成厌恶,起初还只是些微的,后来越来越强烈。我躲进自己的帐篷里,关上纱门,但夏天快来了,天已经暖了;我没法在帐篷里待太久。我到昆人村里采访妇女,但回来时,妮萨经常还在。她的声音持续在营地回荡。我没法视而不见,那种几乎赤裸裸的指责直接扑进耳朵里。我感到自己需要有个地方可以躲她,捂住耳朵和眼睛,不停也不反应。我得采取对策了。
尽管 Shostak 表达出了对妮萨的反感,但她始终抱着希望得到深入回答的问题——
我坦诚告诉她们我是什么人,我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刚结婚,在爱情、婚姻、性和身份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困惑挣扎,从根本上,我最想知道的是女人这一身份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我问她们身为妇女对她们意味着什么,什么在她们的生命里是重要的。
而正是这些问题,在她 20 个月的田野后期再次将她指引到了妮萨身边,而这一次,她发现妮萨又是如何善于讲述故事,扣人心弦、充满魅力,这些故事「有时蕴含了人类生活最微妙也最复杂的经验,有时揭示了人皆有之的复杂情愫」,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她与妮萨都彼此动情——两人的缘分就此结下。后来,离开非洲的 Shostak 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返回非洲,她坦诚,一次次返回非洲意在寻找自我、理解自我。妮萨的故事不是一个用于实现某个世俗目的的工具,尽管 Shostak 确实因此获利,但 Shostak 始终带着从自我出发的问题,作为一个具有各种情感的「真正的人」与另一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样情感充沛的「真正的人」发生着「亦远,亦近」的距离关系。正是这样的努力使得人类学的讲述如此悠远深长。
来自《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的批判 #
James Laidlaw 认为,James Clifford 在《写文化》中对 Greetz 的批判是基于「选择性地将人类学史呈现为占支配地位的民族志写作类型的交替更迭,并且强调民族志工作者他/她自身如何在文本中得到体现」,而忽略了民族志文本的实质内容。
这种叙述是通过对民族志进行分类来建构的,同时它也是一种进步叙事与道德评判,尽管克利福德否认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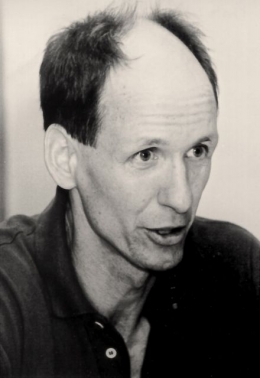
Clifford 序列般地呈现出了一系列的民族志:
- 参与式观察者的民族志:以 Malinowski 为典例,表现为对一手资料的描述,它们由亲身参与所描述事件的人类学家写成,表现出一种宽松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它们还关注语言和翻译问题,并且不论主题焦点或理论取向如何,都采取一种整体主义的表征策略。
- 阐释性民族志:如 Greetz 的《深层游戏》,这类民族志被认为通过一系列逃避和不诚实的行为来摆脱其与政治共谋导致的后果。而这种共谋或被视为「为了帝国统治的利益,欧洲人对非欧洲社会的知识被系统性地扭曲和伪造,对原住民进行讽刺与诽谤,以此作为压迫他们的借口,并将图式化的分类强加于他们,以之作为胁迫和控制的辅助性手段」,「关于『异域』社会的人类学著作与殖民知识/权力的政治统治坑瀣一气,这在某些情况下或许是无意识的,但仍然无法避免」。
- 对话式民族志:这类民族志被视为对过去民族志政治共谋的回应——一种「拯救之道」。民族志工作者的「位置性」直接在文本中体现出来,同时呈现了与信息提供者对话生成「资料」的情境与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提供者的声音也得以被倾听。这意味着这类民族志是人类学家与一个人或几个人之间对话的记录。 [7]但这一类民族志仍然被认为具有共谋性,因为人类学家仍然保留编辑的控制权,因此掌握着呈现他人声音的权力——它被认为必然是殖民主义的、压迫性的和扭曲的。
[7] Laidlaw 在参考文献中提供了几篇对话式民族志:分别是 Paul Rabinow 的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1977)(中译本《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Vincent Crapanzano 的 Tuhami: Portrait of a Moroccan (1980) , Marjorie Shostak 的 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 (1981)(中译本《妮萨:一名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 Kevin Dwyer 的 Moroccan Dialogues: Anthropology in Quesion (1982)。Rabinow 的《摩洛哥田野反思》给我的印象挺深,希望能将继续这几本对话式民族志都读完。
- 多声部民族志:这一类民族志被认为在文本中放弃或分享著作者控制权的方法,能产生由内部碎片化的不同声音拼接而成的文本。 Clifford 认为,随着这种写作方式的发展,最终将超越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局限,使其成为更加开放、更具参与性以及更活跃积极的文化参与形式。 [8]
[8] 或许可以这样认为,经历「写文化」批判以后,人类学是一门极其重视多重主体对话的学科,在一个话题中,强调不同声音的呈现。我认为,前述所说的「结绳志」文章《反对不负责任的写作——《惹作》在凉山内外的回声》正是在出版界声音以外发出的另一种「声音」。
Greetz 在斯坦福大学的一系列讲座中讲述的内容对来自《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的批判做出了回应,Laidlaw 认为有两层:
第一层涉及民族志写作与人类学真相之间的关系:
格尔茨断然驳斥了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有可能找到一种表达民族志真相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剔除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具有的个体独特性。掘弃作者身份,让民族志主体和资料直接发声的想法,既是一种天真的政治幻想(你无法如此轻易地改变世界),又带着一种不被承认的对实证主义真理观念的留恋(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导致真理「部分」扭曲的原因)。
相反, Lévi-Strauss、Evans-Prichard、Malinowski 和 Benedict 之所以被视为极具独创性和影响力的人类学家,正在于他们创造了新的叙述人类学真相的形式。总而言之, Greetz 认为,《写文化》的诗学是过于简单化的,而政治又是幼稚和不切实际。
第二层是我认为比较精彩的,Greetz 围绕着 Malinowski 的日记展开,提出了「日记病」的概念,认为来自《写文化》的批评、焦虑和担忧,其实源于陷入了类似于 Malinowski 的「日记病」,即想要直接获得研究主体的心灵真相,强迫性地试图让读者相信自己对信息提供者的主观认同的深度以及他们的政治情感的纯洁性。
格尔茨的主要观点是,从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里拐弯抹角地表达出来的焦虑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与研究主体缺乏共情感到苦恼不已——他的孤独、挫折、爆发出来的愤怒与怨恨情绪以及他用来缓解这些怨恨所采用的诋毁性的刻板印象与亵渎性言辞——它们之所以让马林诺夫斯基如此感到恐惧,是因为它们直接暴露了他的人类学真相观存在的缺陷。马林诺夫斯基天真的现实主义作风使他希望有一种语言能直接运用于他希望描述的现实。他对心理因素的重视使他认为,若要理解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文化,就必须深入了解作为个体的特罗布里恩人的心灵奥秘。因此,马林诺夫斯基对权威的宣称以及对自己的分析的正确性的信心似乎并不取决于他的观察与论证的质量,而是取决于他能够与特罗布里恩人保持的个人关系以及他能够与他们建立的心理认同程度;不是取决于专业技能与智识,而是取决于无可比拟的敏感性与不容置疑的道德操守。 [9]
[9] 原文无加粗,加粗字体为博主设置。
Greetz 回应的第二层「日记病」打动我的地方在于,他用文字将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复杂的心境表述出来——离开西埠村前,我认为我在那儿待了四个多月,那便一定得「看见什么」、一定要有所收获、一定要书写出某种文字——这或许可以被视为所谓的「人类学真相」。我可能确实没能融入田野,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也不清楚自己究竟要了解什么,但出于对这门学科的「虔诚」和「迷信」——这在事实上似乎转化为了某种自我感动和掩护——我试图竭力表达我与当地人建立了如何深入的关系,我们之间的情感和羁绊又是如何动人。这何尝不是一种对「政治情感的纯洁性」的追求。但这并不诚恳,给予我的也只有「刻意」感,事后回想只有「不愿意再深入回想」,相比于此,我更想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为什么不能直面自我,坦诚自己的不足和无能?
参考资料 #
- 春花制造机:粪便|厚描,斗鸡,反“反文化主义”,公众号:脂肪苦難, https://mp.weixin.qq.com/s/dOykQkR5wYQkHuPemi3CsQ ,2023-06-24
- 春花制造机:散记 | 作为理论的田野调查:经验与距离的拓扑学,公众号:脂肪苦難, https://mp.weixin.qq.com/s/9tWIkkOOrA0FGOUYv0ecLQ ,2023-06-06
- 杰里·D.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欧阳敏 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07版
-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 译,译林出版社,2014-08版
- 玛乔丽·肖斯塔克:《妮萨:一名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杨志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01版
- 马泰·坎迪亚:《剑桥大学人类学理论十五讲:人类学理论的流派与风格》,王晴锋 译,金城出版社,2024-08版
-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07版